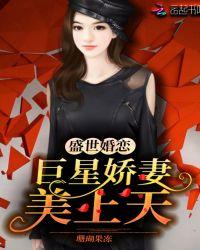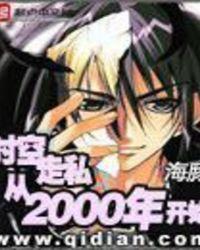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3章(第1页)
家庭戏班的建立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不仅要多方物色优伶,延聘教习训练女乐优童,还要由家班主人寻访或自撰剧本,营造演出用的场所,或戏台,或厅堂,或戏船,此外还要为演出张罗筵席,探讨技艺,参与竞争……这一切使得家班主人不能不把日常精力的极大一部分都耗费在昆曲上,并力求使自己也成为一个昆曲行家。
如果这样的事情只是发生在个别富豪之家那倒也罢了,但事实上这在明代后期已成为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一种戏剧审美方式如此强悍地闯入这么多上层家庭的内部,成为他们不可缺少的生活嗜好,甚至成为他们争相趋附的生活方式,这在世界戏剧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在以往的中国戏曲史研究上,这种家庭戏班常常被斥之为&ldo;世纪末&rdo;士大夫阶层奢侈、糜烂的生活表征,这是以社会学取代了戏剧学。
从戏剧学的视角来看,家庭戏班呈现了昆曲艺术社会渗透力的某种极致,也透露出昆曲艺术的美学结构与中国宗法伦理社会结构之间的深层对应,与庭院式演出空间之间的深层对应,与士大夫文化心态之间的深层对应。
其三,职业昆班的高度发达和备受欢迎。
职业戏班在万历初年光苏州一郡就已达数千人,以后则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这么多人靠昆曲演出为生,正是因为社会大众都痴迷着昆曲。
据记载,当时有很大一批人到了几乎每天必须看昆曲的地步,曾引起研究者兴趣的明潘允端《玉华堂日记》和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就清楚地记述了当时演剧和观剧的频繁度,人们好像天天都在观看昆曲,读了不免让今人大吃一惊。
日记还表明,这种日日看戏的习惯不仅普及于苏州、杭州、扬州、上海,而且同样也出现于北京和天津。
这种习惯势必又使职业昆班的演出每每人满为患,据张岱《陶庵梦忆》记载,杭州余蕴叔戏班的一次演出曾出现过&ldo;万余人齐声吶喊&rdo;的壮观景象,而苏州枫桥杨神庙一次职业戏班的演出竟然达到&ldo;四方观者数十万人&rdo;。
陆文衡在《啬庵随笔》中也说苏州一带看戏到了&ldo;通国若狂&rdo;的地步。
社会各阶层对职业昆班的这种狂热比虎丘山中秋曲会的热闹有更深的意义,因为这已不仅仅是以唱曲为主而是完全面对完整的演出了,而且不是一年一度而是天天皆然;也比家庭戏班的活动更有价值,因为这已冲破高墙深院的局囿而直接与千百万民众融合在一起了,能剔除某种家庭戏班演出所不可避免的偶然性而更准确地反映昆曲在当时的社会实现形态。
千万双挑剔的眼睛和日复一日的不停演出使职业昆班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一大批优秀的演员脱颖而出。
因此,人们对职业昆班的痴迷是最有研究价值的一种痴迷。
以上三个方面证明,昆曲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时间地酿发过惊人的观赏热潮和参与热潮,其程度远超先于它的元杂剧和宋元南剧,以及后于它的花部诸腔,甚至在现代也未曾有任何一种观剧热潮能与之相比肩。
这一事实已可证明它作为一种戏剧范型比其它范型曾经更透彻、更深刻地锲入过我们民族的集体审美心理,是我们民族精神历程中最重要的审美对象之一。
在戏剧领域,离开了观众轰动而所谓的&ldo;重要&rdo;是单向的&ldo;重要&rdo;,是没有造成事实的&ldo;重要&rdo;,因此也是一种虚假的&ldo;重要&rdo;,不应该占据多大的历史地位。
现代戏剧学只重视在社会历史上真正实现了的戏剧,或者说真正融入了社会历史、与社会历史不可分割的戏剧,从这种观念出发,昆曲的历史地位也就明显地凸现出来了。
社会性痴迷是一种很值得玩味的文化现象。
一切艺术都在寻找着自己的接受者,而一切接受者都在寻找着接受对象,当一种艺术与一个群落终于对位并产生如胶似漆的互吸力的时候,当它们交融一体而几乎物我两忘的时候,便产生了社会的痴迷。
如前所说,在中国艺术史上唐诗和书法都产生过长时间的社会性痴迷,社会的精神翅翼围着它们转,人生的形象、生活的价值都与它们不可分,为着一句诗、一笔字,各种近乎癫狂的举动和匪夷所思的故事都随之产生,而社会大众竟也不觉为怪,由此足可断定唐诗和书法在中国的古典审美构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昆曲作为一种在广阔范围内引起了社会性痴迷的艺术门类繁荣了两百多年,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
05、上层文化的高浓度介入
空前的社会普及必然牵动上层文化界,上层文化界可以隔岸观火,也可以偶尔涉足,这就只能使社会普及停留在原生态的阶段;如果上层文化界终于按捺不住,浩荡介入,而且慷慨地把自身的文化优势投注其间,那么就会产生惊天动地的文化现象了。
昆曲,是世俗艺术中吸纳上层文化最多的一个门类。
在昆曲之前,北杂剧也达到过很高的文化品味,也出现过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这样的文化大师,但是如果北杂剧的创作队伍与昆曲的创作队伍作一个整体比较就会发现,昆曲创作队伍里高文化等级的人要多得多。
大致说来,北杂剧创作队伍中的骨干和代表性人物是士大夫中的中下层知识分子,而昆曲创作队伍中的骨干和代表性人物是士大夫中的中上层知识分子,这是不同时代背景和社会风气使然,也与两种戏剧范型发达的时限长短有关。
元代杂剧作家中有进士及第的极为罕见,而明代以进士及第而做官的剧作家多达二十八位。
科举等级当然不等于文化等级,但这一现象充分证明了明代的上层知识界与戏剧活动的密切关系。
上层文化人排除了自己与昆曲之间的心理障碍,不仅理直气壮地观赏、创作,甚至有的人还亲自扮演,粉墨登场,久而久之,昆曲就成为他们直抒胸臆的最佳方式,他们的生命与昆曲之间沟通得十分畅达,因此他们也就有意无意地把自身的文化感悟传递给了昆曲。
总的说来,昆曲与元杂剧相比,创作者的主体人格传达得更加透彻和诚恳了。
尽管也有不少令人厌烦的封建道学之作,但就其最杰出的一些代表作而言则再鲜明不过地折射当时中国上层知识界的集体文化心理。
《清忠谱》所表现的取义成仁的牺牲精神,《长生殿》所表现的历史沧桑感和对已逝情爱的幽怨缅怀,《桃花扇》所表现的兴亡感与宗教灭寂感,尤其是汤显祖的《牡丹亭》从人本立场出发对至情、生死的试炼和感叹,都是上层知识界内心的真诚吐露,我们如果把这几个方面组合在一起,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几根支柱。
这几部传奇作品与《红楼梦》等几部小说加在一起,构成了明清两代一切文化良知都很难逃逸在外的精神感应圈。
直到今天,我们若要领略那个时期的精神气质和文化风韵,这几部作品仍是极具典型意义的课本。
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元杂剧还是花部诸腔都无法与之相比。
元杂剧当然也具有足够的精神强度,关汉卿式的强烈和王实甫式的艳丽都可以传之千古,本人曾在拙著《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一书中论证,元杂剧在精神上有两大主调,第一主调是倾吐整体性的烦闷和愤怒,第二主调是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并由这两大主调伸发出真正的悲剧美和喜剧美;但不能否认,这种情绪吐露还还不是对主体精神领域的系统开掘,在深度上还是比不上《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
至于花部诸腔,以生气勃勃的艺术面貌取代日渐疲惫的昆曲自有天然合理性,但在剧作精神上大多浅陋得多,除了鲜明的道德观念,因果报应期待和某些反叛意识外就没有太多更深入的内涵了。
跻身在花部的热闹中,《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的意蕴和感慨很可能显得过于执着、凝重而&ldo;落伍&rdo;了,但&ldo;落伍&rdo;也保持着自身的高度。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留守乡村的少年曾呓
- 暗火白芥子
- 把妻子献给了行长中国必胜
- 二哈和他的白猫师尊肉包不吃肉
- 差错【兄妹H】一包熏咸鱼
- [综漫]夏目是个小团宠柠檬碰汽水
- 年代文女配自救指南清越流歌
- 奇洛李维斯回信清明谷雨
- 反派:师尊师姐求你们了天行见道
- 今天也没能扬帆起航春风遥
- 我在古代搞科研晴空之下
- 浸梦(兄妹H)澄金银
- 踏星随散飘风
- 聊骚(公媳出轨)凉凉
- 奇迹/奇跡(出书版)+番外林珮瑜
- 萧煜凤九颜凤九颜萧煜凤薇蔷
- RPG,但木叶村物语梨茄子
- 生生[病娇 灵异]雪莉
- 全球基因改造白吃大锅饭
- 秘闻(公媳)向雾
- 穿越HP多木木多
- [全职乙女]攻略进行中坑王绯
- 觅食(父子丼)小圈降临
- 石小小的快乐生活(高辣、、等)kfbjk
- 十日终焉杀虫队队员
- 当我穿成历史名人的宠物置业
- 末世:姑娘莫慌,我物资够用百年彭不易
- 被好感度包围的我犹如遭遇仇杀[西幻]三千世
- 生生[病娇 灵异]雪莉
- 末世半岛:我的丧尸女友四块钱的可乐
- 妹控(兄妹,H)莉莉香
- 重生之毒妃梅果
- 长生苟道:开局吹唢呐,送葬修仙雄鸡一唱两年半
- 优质肉棒攻略系统(高辣文)寀小花
- 我的楔姐姐佚名
- 我和校花有个约会大大洋洋
- 幼女天空下_山村老师 作者:万恶我为首击水三千
- 今天也没能扬帆起航春风遥
- 替嫁妻子走后,剑尊道心破碎了草灯大人
- 借种向雾
- 呦呦爱吃肉(乱伦 np)奶味大肉棒
- 淫荡幼女一条狗
- 玄幻:勾栏听曲的我,模拟成神第二十五时
- 病欲(兄妹H)食肉大小姐
- 缚剑(修仙H)非卿
- 谁把谁当真水千丞
- 重生在折辱清冷男主前妖妃兮
- 呦呦爱吃肉( )奶味大肉棒
- 觅食(父子丼)小圈降临
- 说好的恐同呢?路晚星
- 苏辰影后老婆疯狂拍戏我摆烂成为热搜焦点全集免费阅读海浪无声
- 苏城小说在线阅读凉小城
- 雪夜活埋后,我夺了假千金凤命柠檬小丸子
- 新婚夜换亲清冷指挥使沦陷了番外最新章节福气到
- 太太让位白月光父子夜夜求原谅盛暖厉庭舟森火
- 重生逆袭成仙开局撞破公主做歌姬无删减无弹窗孤雨随风
- 林萱沈逸辰新婚夜换亲清冷指挥使沦陷了全集免费阅读福气到
- 宝藏主播:榜一竞争太激烈有猫腻
- 雪夜活埋后我夺了假千金凤命盛锦初盛嫣嫣柠檬小丸子
- 叶川小说在线阅读狐狸爱美人
- 叶川说好扫黄你直接枪斗术点满全集免费阅读狐狸爱美人
- 许逐月顾朝青小说在线阅读末之未央
- 苏辰小说在线阅读海浪无声
- 万道熔炉诀无删减无弹窗番薯烤地瓜
- 影后老婆疯狂拍戏我摆烂成为热搜焦点无删减无弹窗海浪无声
- 林天叶清涟重生逆袭成仙开局撞破公主做歌姬全集免费阅读孤雨随风
- 说好扫黄你直接枪斗术点满无删减无弹窗狐狸爱美人
- 说好扫黄你直接枪斗术点满番外最新章节狐狸爱美人
- 主角林棠棠秦墨安小说笔趣阁无弹窗枫林月熹
- 影后老婆疯狂拍戏我摆烂成为热搜焦点番外最新章节海浪无声
- 权道之夫人们太给力了番外最新章节纯情阿良
- 新婚夜换亲清冷指挥使沦陷了无删减无弹窗福气到
- 出宫前夜,疯批帝王后悔了素律
- 主角林岁秦牧小说笔趣阁无弹窗不要吃花卷
- 和亲皇子女帝逼我去北荒屯粮练兵我称皇无删减无弹窗凉小城